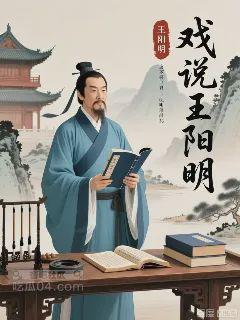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AA+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
繁
第五章
2018-5-26 06:02
“大和尚有家吗?”
“和尚我有佛家,也有俗家。”
“大和尚俗家可安好?”
“和尚我家中老母尚在”
“哦,原来如此。”王守仁点了点头,突然一阵思绪如闪电般划过,他话锋一转,问了一句始料未及的话,“你想你母亲么?”
佛堂沉默了,树叶沙沙的落在禅院,大和尚苦笑一声,叹道,“惭愧惭愧,甚是想念。”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来自己苦修三年之后竟然还是眷恋着自己的俗家,眷恋着自己的母亲,和尚觉得深感惭愧。然而王守仁一本正经的说:“想念自己的母亲是人的本心,这有什么好惭愧的呢?人只有先做人才能成佛,如果连一个最基本的人都做不好,又怎么可能悟得大道成仙成佛呢?”王阳明的一番话说的和尚泪流满面,第二天这位和尚就还俗回家,向自己的老母亲尽孝去了。
王守仁心中愕然,他终于觉得自己隐约看到了一缕光芒,那是圣贤之光。如果说把佛看作是得道,而得到即为圣人,那么之前的逻辑就变成了这样,人只有先做人才能得道,如果连一个基本的人都做不好,又怎么可能悟得大道成为圣人呢?于是那个大多数人并不太熟悉的王守仁先生,向名垂青史的王阳明先生迈出了第一步,他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如何,人性依旧存在,无论如何,人性永远不灭。
流放贵州
大和尚还俗回家孝敬母亲去了,王阳明也渐渐意识到朱熹对“理”和“欲”的处置方式是欠妥的。天理存在万物,人欲存在内心,人的的确确有着自己的欲望,这些欲望有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是值得尊崇的,比如和尚对老母亲的孝心,比如恋人之间海枯石烂的爱情,比如朋友之间刎颈莫逆的友情,这些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用强大的天理来压制来消灭呢?更何况还根本就消灭不掉。
距离真相越来越近的王阳明又遇到了瓶颈,他发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妥当,也发现了天理和人欲之间未必就是对立与矛盾的关系,然而“理”已然还是在的,可是在哪儿呢?只有真真切切的抓住这个“理”,才能真真正正得成为圣贤。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程朱说“理”在万物中,于是饶了一大圈,王阳明还是只有那一个老办法,那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到猴年马月是个头的格物致知。日子就这么一点点过去,格物依旧没格出什么好东西来,然后经过这一次的顿悟,王阳明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理”的蛛丝马迹。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带着康复的身体与崭新的收获,三十二岁的王阳明重新回到在职公务员的队伍中,在监察御史巡抚山东的陆称邀请下,他主持了山东的乡试,为朝廷选拔了不少具有实干精神的人才,九月抵京,担任了正六品兵部武选司主事。
这次到了北京,王阳明开始向他的朋友们宣传自己的新观点新感悟,老朋友何景明、李梦阳等都是他的忠实信徒,这些崭新的学术主张逐渐传播开来,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文人向其讨教,在交流中继续王阳明正逐步完善着自己的学说。应该说此时的王阳明官场上较为顺利,学术上也有了自己崭新的造诣,是人生的顺风期,然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这时候的明朝政坛产生了剧烈的震荡,正直的王阳明摊上大事了。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大明帝国的优秀皇帝,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帝国主义战士,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明孝顺宗朱佑樘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这位蛮女之子在他十八年的执政生涯中为朝廷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他一生勤政爱民,为后世所尊敬。然后他这辈子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对自己儿子的培养,以至于他儿子最后的名气比他还大得多。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十五岁的小朋友朱厚照登继承大统是为明武宗,明武宗作为大明历史上头号玩家在时任司礼监太监刘瑾的忽悠下开始了他吃喝玩乐的皇帝生涯,在皇上今天来个游龙戏凤,明天来个豹房一日游的局面下,太监刘瑾用诡计赶走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正直的大臣,正式接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大臣们为被赶走的两位前辈抱不平,纷纷上书挽留二人并且痛陈刘瑾十大罪状要求法办,监察御史薄彦征、南京给事中戴铣带头上书,一共二十多人,可谓声势浩大,然后太监是不跟你讲道理的,权监是不跟你讲人性的,刘瑾一声令下,对二十多名大臣施以廷杖,所谓廷杖就是当庭脱了裤子轮着大棒往下打,文臣的身子骨通常都不强健,戴铣当场就被活活打死。
看到这二十多名忠义之士遭到权贵的无端迫害,大臣们更加义愤填膺,又开始了第二轮上书,这一次王阳明也参加了,他是个小官,他更是一个正直而有道德的君子,哲学家王阳明先生并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文人,他愤怒得写下了奏折。其实第二次上书大多数人都是要求对之前的二十多个大臣从轻处理,为挨了板子的老同志求情,然后王阳明与大家不同,他看到了刘瑾的黑暗与邪恶,不单单要求朝廷释放朝臣还义正言辞地指责了刘瑾“权监误国”。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王阳明展现了他崇高的气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顺利领到了四十廷杖,不仅如此在挨了打回去后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吏部的通知,鉴于王阳明为罪臣开脱且公然污蔑朝廷大员,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免去王阳明同志兵部武选司主事的职务,从即日起左迁贵州龙场驿驿丞。
我们都知道,古人以右为尊,右迁那是晋升,左迁自然就是降职,王先生怒骂当朝头号实权派,被降职是必然的了,到底降了多少呢?我们之前提到过,王阳明此前担任兵部武选司主事,这是一个六品正厅级干部,而他的新职务又多大呢?这个职务放到现在叫做贵州龙场招待所所长,龙场在现在的贵州省修文县,在明朝这里是相当偏僻的地方,说是招待所基本上也招待不到多少人,因为需要被招待的人是不会来龙场的,来了龙场的都是不需要去招待的。
原先大小还是个六品,而这个所长几品呢?正确的说法是没品,明朝的官方称谓叫做不入流,也就是说你还是公务员,但是你已经比最小的领导职务还小的,拿现在的话说大致相当于个非领导职务,估计也就介于科员和副科级之间,勉强算个股长。而老父亲王华也跟着挨了批评,“擢升”南京吏部尚书,当了一个没有实权只负责养老的正部级干部,被排挤出了京城。
辉煌之后总是黑暗,王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低谷,灰溜溜的带着几个仆从朝着贵州行进,太监刘瑾着实是个心肠狠毒的人,被王阳明一通臭骂心里实在是气不过,于是便特意安排了心腹杀手准备在路上杀掉王阳明,一来解了气而来除了后患。然而每天老老实实格东格西的王阳明本质上并不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早就料到了以刘瑾的心胸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在走到钱塘江时他把自己的衣服冠冕全都丢进江中,然后再写了一封声泪俱下怒斥奸臣的遗书放在岸边,大意就是权监必遭天谴,我都被你害得不想活了,我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的内容。果然尾随其后的杀人听闻王阳明已经自杀了便回去交差了。王阳明换成商船到了福建,看着巍峨的武夷山,联想到自己心酸的命运,于是在山下墙壁题诗一首:
“和尚我有佛家,也有俗家。”
“大和尚俗家可安好?”
“和尚我家中老母尚在”
“哦,原来如此。”王守仁点了点头,突然一阵思绪如闪电般划过,他话锋一转,问了一句始料未及的话,“你想你母亲么?”
佛堂沉默了,树叶沙沙的落在禅院,大和尚苦笑一声,叹道,“惭愧惭愧,甚是想念。”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来自己苦修三年之后竟然还是眷恋着自己的俗家,眷恋着自己的母亲,和尚觉得深感惭愧。然而王守仁一本正经的说:“想念自己的母亲是人的本心,这有什么好惭愧的呢?人只有先做人才能成佛,如果连一个最基本的人都做不好,又怎么可能悟得大道成仙成佛呢?”王阳明的一番话说的和尚泪流满面,第二天这位和尚就还俗回家,向自己的老母亲尽孝去了。
王守仁心中愕然,他终于觉得自己隐约看到了一缕光芒,那是圣贤之光。如果说把佛看作是得道,而得到即为圣人,那么之前的逻辑就变成了这样,人只有先做人才能得道,如果连一个基本的人都做不好,又怎么可能悟得大道成为圣人呢?于是那个大多数人并不太熟悉的王守仁先生,向名垂青史的王阳明先生迈出了第一步,他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如何,人性依旧存在,无论如何,人性永远不灭。
流放贵州
大和尚还俗回家孝敬母亲去了,王阳明也渐渐意识到朱熹对“理”和“欲”的处置方式是欠妥的。天理存在万物,人欲存在内心,人的的确确有着自己的欲望,这些欲望有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是值得尊崇的,比如和尚对老母亲的孝心,比如恋人之间海枯石烂的爱情,比如朋友之间刎颈莫逆的友情,这些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用强大的天理来压制来消灭呢?更何况还根本就消灭不掉。
距离真相越来越近的王阳明又遇到了瓶颈,他发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妥当,也发现了天理和人欲之间未必就是对立与矛盾的关系,然而“理”已然还是在的,可是在哪儿呢?只有真真切切的抓住这个“理”,才能真真正正得成为圣贤。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程朱说“理”在万物中,于是饶了一大圈,王阳明还是只有那一个老办法,那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到猴年马月是个头的格物致知。日子就这么一点点过去,格物依旧没格出什么好东西来,然后经过这一次的顿悟,王阳明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理”的蛛丝马迹。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带着康复的身体与崭新的收获,三十二岁的王阳明重新回到在职公务员的队伍中,在监察御史巡抚山东的陆称邀请下,他主持了山东的乡试,为朝廷选拔了不少具有实干精神的人才,九月抵京,担任了正六品兵部武选司主事。
这次到了北京,王阳明开始向他的朋友们宣传自己的新观点新感悟,老朋友何景明、李梦阳等都是他的忠实信徒,这些崭新的学术主张逐渐传播开来,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文人向其讨教,在交流中继续王阳明正逐步完善着自己的学说。应该说此时的王阳明官场上较为顺利,学术上也有了自己崭新的造诣,是人生的顺风期,然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这时候的明朝政坛产生了剧烈的震荡,正直的王阳明摊上大事了。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大明帝国的优秀皇帝,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帝国主义战士,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明孝顺宗朱佑樘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这位蛮女之子在他十八年的执政生涯中为朝廷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他一生勤政爱民,为后世所尊敬。然后他这辈子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对自己儿子的培养,以至于他儿子最后的名气比他还大得多。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十五岁的小朋友朱厚照登继承大统是为明武宗,明武宗作为大明历史上头号玩家在时任司礼监太监刘瑾的忽悠下开始了他吃喝玩乐的皇帝生涯,在皇上今天来个游龙戏凤,明天来个豹房一日游的局面下,太监刘瑾用诡计赶走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正直的大臣,正式接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大臣们为被赶走的两位前辈抱不平,纷纷上书挽留二人并且痛陈刘瑾十大罪状要求法办,监察御史薄彦征、南京给事中戴铣带头上书,一共二十多人,可谓声势浩大,然后太监是不跟你讲道理的,权监是不跟你讲人性的,刘瑾一声令下,对二十多名大臣施以廷杖,所谓廷杖就是当庭脱了裤子轮着大棒往下打,文臣的身子骨通常都不强健,戴铣当场就被活活打死。
看到这二十多名忠义之士遭到权贵的无端迫害,大臣们更加义愤填膺,又开始了第二轮上书,这一次王阳明也参加了,他是个小官,他更是一个正直而有道德的君子,哲学家王阳明先生并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文人,他愤怒得写下了奏折。其实第二次上书大多数人都是要求对之前的二十多个大臣从轻处理,为挨了板子的老同志求情,然后王阳明与大家不同,他看到了刘瑾的黑暗与邪恶,不单单要求朝廷释放朝臣还义正言辞地指责了刘瑾“权监误国”。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王阳明展现了他崇高的气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顺利领到了四十廷杖,不仅如此在挨了打回去后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吏部的通知,鉴于王阳明为罪臣开脱且公然污蔑朝廷大员,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免去王阳明同志兵部武选司主事的职务,从即日起左迁贵州龙场驿驿丞。
我们都知道,古人以右为尊,右迁那是晋升,左迁自然就是降职,王先生怒骂当朝头号实权派,被降职是必然的了,到底降了多少呢?我们之前提到过,王阳明此前担任兵部武选司主事,这是一个六品正厅级干部,而他的新职务又多大呢?这个职务放到现在叫做贵州龙场招待所所长,龙场在现在的贵州省修文县,在明朝这里是相当偏僻的地方,说是招待所基本上也招待不到多少人,因为需要被招待的人是不会来龙场的,来了龙场的都是不需要去招待的。
原先大小还是个六品,而这个所长几品呢?正确的说法是没品,明朝的官方称谓叫做不入流,也就是说你还是公务员,但是你已经比最小的领导职务还小的,拿现在的话说大致相当于个非领导职务,估计也就介于科员和副科级之间,勉强算个股长。而老父亲王华也跟着挨了批评,“擢升”南京吏部尚书,当了一个没有实权只负责养老的正部级干部,被排挤出了京城。
辉煌之后总是黑暗,王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低谷,灰溜溜的带着几个仆从朝着贵州行进,太监刘瑾着实是个心肠狠毒的人,被王阳明一通臭骂心里实在是气不过,于是便特意安排了心腹杀手准备在路上杀掉王阳明,一来解了气而来除了后患。然而每天老老实实格东格西的王阳明本质上并不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早就料到了以刘瑾的心胸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在走到钱塘江时他把自己的衣服冠冕全都丢进江中,然后再写了一封声泪俱下怒斥奸臣的遗书放在岸边,大意就是权监必遭天谴,我都被你害得不想活了,我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的内容。果然尾随其后的杀人听闻王阳明已经自杀了便回去交差了。王阳明换成商船到了福建,看着巍峨的武夷山,联想到自己心酸的命运,于是在山下墙壁题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