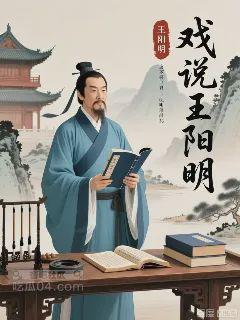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AA+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
繁
第四章
2018-5-26 06:02
他在龙泉山下的阳明洞里专研学问,继续学习着他的文武韬略。王守仁因此自号阳明,后人又叫他王阳明,他在龙泉山创建了个文学社团,周边地区的文人都慕名而来,大家畅谈国是,吟诗作赋,就连退了休的老省长前浙江从二品布政使魏瀚也兴致冲冲得加入了社团,他曾是王华的诗友,他的父亲又是王伦的诗友,魏王两家算是世交按辈分他应当是王阳明的伯伯,然而他却与晚辈王守仁成为了往年之交,在对诗中常常甘拜下风连连叹道:“老夫当退数舍。”一时在文坛传为佳话。此时此刻的王守仁经历了命运的挫折,开始对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进行了思考,这种心情在《次魏五松荷亭晚兴》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风光于我能留意,
世味酣人未解醒。
长拟心神窥物外,
休将姓子重乡评。
飞腾岂必皆伊吕,
归去山田亦可耕。
青年王守仁的世界里有了“田园世界”与“仕途世界”,他又指出了人生并不是只有入仕一条路才有意义,“飞腾岂必皆伊吕”说并不是人人都要成为伊尹姜子牙这样的治世能臣,也可以回归田园享受山水之乐,在爷爷竹轩翁王伦的教导下王守仁的心性显得十分平和。
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王华来信叫停了王守仁的社团活动,因担心儿子在家乡没有名师指点,便命他早早收拾行李赶赴京城准备考试,王守仁只好别了妻子和社团的好友前往北京。鉴于前两次高考失利心中有愧,这一次王守仁在父亲的叮嘱下乖乖得开始了自己踏踏实实的学习生活,然而每次空闲出居庸关,“土木堡”三个大字如同一把利刃扎在他的心口,朝廷虽然有武科举考试,但是选拔而来的大多都是以一当十的武林高手,虽然单兵作战能力强,但并不具备优秀的统帅能力,于是在熟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他丝毫不放松自己对兵法战略的研究,他是一个好学乐学善学的人,任凭你三教九流,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王守仁都锲而不舍的去专研揣摩,一年下来,王守仁已经成为了非常杰出的文武全才。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今非昔比的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笔试中他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在接下来的面试中他被明孝宗钦点为二甲,虽说不及王华状元来的威风,好歹也算是有了个交代,比起那些奋斗一辈子还是个秀才的同志实在是很幸运了。由于在二甲中排名不够高,王守仁没有混进明代官场上前途无量的储备干部训练营翰林院而是被分配到个工部担任观政。
尽管这是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责任心很强的王守仁依旧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在任职期间他曾担任威宁伯王越坟墓修建工程队的监工,在这期间他在不违反朝廷陵寝建制规定的情况下把威宁伯墓修的大方端庄,家属们十分满意,纷纷赞扬王守仁处事得体办事能力强,威宁伯的儿子还把自己已故父亲的配剑赠送给王守仁以表感激与尊重,从此这把寒光凛凛的宝剑就一直跟随着王守仁。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在办好督造威宁伯陵寝这一差事后,朝廷上下正在热议西北边疆瓦刺部族的边防问题,瓦刺部族骁勇善战且和大明帝国有着土木堡的深仇大恨,如今扬言要举兵来袭着实让朝廷忙的焦头烂额。
王守仁自从幼年跟随父亲出居庸关,见识了北方的疆域后便一直很留心军事与国防问题,他经过一整夜的思考,写下了着名的《筹边八事》上书朝廷,其中详尽的分析了大明帝国现在的国防重点,指出了边防部队的弊病,由于其针对性较强,比较有实用性,英明的明孝宗看了之后龙颜大悦,擢升王守仁担任正六品刑部云南司主事,二十九岁的王守仁成为了政法系统的正厅级干部,从此他告别了以前在京城做办公室的工作,开始了在全国各地出差审案的生活。
人性不灭
按理说,少年得志的王守仁应该高兴才是,其实他自己心中并不觉如此,因为他不仅仅是大明王朝的官僚,他还是一个思想者,有着崇高梦想的思想者。从守仁格竹之后,他依旧坚持着这个他已经不全信的方法,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从二十岁格到了二十九岁,他丝毫没有豁然,反而他更加的痛苦。因为这九年来他深切的感受到,朱大圣人所说的神奇方法,似乎真的没什么作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朱子作为圣人也有。朱子把我们的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就好比太极中的黑与白,交织着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一个叫做“理”一个叫做“欲”。先前我们提到了,朱子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是宇宙中一个绝对正确的真理,只要人人都遵从了这个真理,那么天地就和谐了,万物就有爱了,一切的问题都不存在了,不管是违反乱纪的制度问题还是嗔痴贪色等到的问题,一切都是美好的。
可惜的是我们的世界还有“欲”在,这个“欲”可以大致的理解成欲望,本来世界是美好的是又秩序的,奈何我们人类偏偏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私欲,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的太平盛世没有了,被欲搅的一塌糊涂。
那么怎么办呢?在程朱理学中有一句着名度极高的话,让人又爱又恨的话,这句话就是朱熹同志解决棘手问题的办法:“存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的意思不单单只是叫失去丈夫的妇女们不要改嫁,它告诉我们要用理性的客观的主宰万物的“理”,去对抗去消灭我们主观上心中的“欲”,只有这样做,世界才和谐。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追求那个高远的绝对正确的“理”,然后放弃掉我们自身狭隘的“欲”。
鉴于朱熹是我们大明王朝皇帝陛下理论上的祖宗,鉴于大明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这套理论成为了大明官方的核心价值体系,不单是各级政府机构按此价值观办事,各级教育系统也按此价值观教书育人,如果说“理”是世界的绝对真理,那么理学在当时的政坛文坛也是绝对真理。经过九年的格物致知,王守仁先生对这个探求“理”的方法产生了动摇,而接下来的事,让他对这个理论体系也产生了怀疑。
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由于身体微恙,王守仁移居杭州静养,面对着淡妆浓抹的绝美西湖他的心情有了难得的轻松,尽管心里的结尚未解开,可能够纵情于山水忘怀心中之忧愁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他抛开了之前消极的情绪,时常往返于各大寺庙书院,与得到高僧或是知名文人畅谈人生,生活颇丰。
有一天王守仁留宿一座古寺,他遇见了一位年老的僧人,那僧人端坐佛堂闭母凝神,一看便是得道之高僧,一旁的小和尚对他说:“这个大和尚从不曾开口说话,也不曾睁眼看人,如此已有三年了。”王守仁沉默了半晌,突然大喝一声,怒斥道:“你这老和尚整天唧唧歪歪说些什么!整天瞪着眼睛眼睁睁得看着什么!”这句话甚有玄机,因为那大和尚明明就三年不曾开口三年不曾睁眼了,和尚大吃一惊,因为这三年来从不曾有一人朝他如此大喝,也不曾有人和他说过如此玄妙的话,于是他缓缓的睁开了眼睛,四目一对,口称:“居士别来无恙。”二人开始了交谈,他们从佛经开始,谈到西湖,又谈到了佛家所言之道,那大和尚果然是一代高僧,对佛法的理解大大超出了王守仁的意料,聊着聊着,王守仁突然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
风光于我能留意,
世味酣人未解醒。
长拟心神窥物外,
休将姓子重乡评。
飞腾岂必皆伊吕,
归去山田亦可耕。
青年王守仁的世界里有了“田园世界”与“仕途世界”,他又指出了人生并不是只有入仕一条路才有意义,“飞腾岂必皆伊吕”说并不是人人都要成为伊尹姜子牙这样的治世能臣,也可以回归田园享受山水之乐,在爷爷竹轩翁王伦的教导下王守仁的心性显得十分平和。
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王华来信叫停了王守仁的社团活动,因担心儿子在家乡没有名师指点,便命他早早收拾行李赶赴京城准备考试,王守仁只好别了妻子和社团的好友前往北京。鉴于前两次高考失利心中有愧,这一次王守仁在父亲的叮嘱下乖乖得开始了自己踏踏实实的学习生活,然而每次空闲出居庸关,“土木堡”三个大字如同一把利刃扎在他的心口,朝廷虽然有武科举考试,但是选拔而来的大多都是以一当十的武林高手,虽然单兵作战能力强,但并不具备优秀的统帅能力,于是在熟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他丝毫不放松自己对兵法战略的研究,他是一个好学乐学善学的人,任凭你三教九流,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王守仁都锲而不舍的去专研揣摩,一年下来,王守仁已经成为了非常杰出的文武全才。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今非昔比的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笔试中他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在接下来的面试中他被明孝宗钦点为二甲,虽说不及王华状元来的威风,好歹也算是有了个交代,比起那些奋斗一辈子还是个秀才的同志实在是很幸运了。由于在二甲中排名不够高,王守仁没有混进明代官场上前途无量的储备干部训练营翰林院而是被分配到个工部担任观政。
尽管这是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责任心很强的王守仁依旧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在任职期间他曾担任威宁伯王越坟墓修建工程队的监工,在这期间他在不违反朝廷陵寝建制规定的情况下把威宁伯墓修的大方端庄,家属们十分满意,纷纷赞扬王守仁处事得体办事能力强,威宁伯的儿子还把自己已故父亲的配剑赠送给王守仁以表感激与尊重,从此这把寒光凛凛的宝剑就一直跟随着王守仁。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在办好督造威宁伯陵寝这一差事后,朝廷上下正在热议西北边疆瓦刺部族的边防问题,瓦刺部族骁勇善战且和大明帝国有着土木堡的深仇大恨,如今扬言要举兵来袭着实让朝廷忙的焦头烂额。
王守仁自从幼年跟随父亲出居庸关,见识了北方的疆域后便一直很留心军事与国防问题,他经过一整夜的思考,写下了着名的《筹边八事》上书朝廷,其中详尽的分析了大明帝国现在的国防重点,指出了边防部队的弊病,由于其针对性较强,比较有实用性,英明的明孝宗看了之后龙颜大悦,擢升王守仁担任正六品刑部云南司主事,二十九岁的王守仁成为了政法系统的正厅级干部,从此他告别了以前在京城做办公室的工作,开始了在全国各地出差审案的生活。
人性不灭
按理说,少年得志的王守仁应该高兴才是,其实他自己心中并不觉如此,因为他不仅仅是大明王朝的官僚,他还是一个思想者,有着崇高梦想的思想者。从守仁格竹之后,他依旧坚持着这个他已经不全信的方法,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从二十岁格到了二十九岁,他丝毫没有豁然,反而他更加的痛苦。因为这九年来他深切的感受到,朱大圣人所说的神奇方法,似乎真的没什么作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朱子作为圣人也有。朱子把我们的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就好比太极中的黑与白,交织着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一个叫做“理”一个叫做“欲”。先前我们提到了,朱子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是宇宙中一个绝对正确的真理,只要人人都遵从了这个真理,那么天地就和谐了,万物就有爱了,一切的问题都不存在了,不管是违反乱纪的制度问题还是嗔痴贪色等到的问题,一切都是美好的。
可惜的是我们的世界还有“欲”在,这个“欲”可以大致的理解成欲望,本来世界是美好的是又秩序的,奈何我们人类偏偏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私欲,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的太平盛世没有了,被欲搅的一塌糊涂。
那么怎么办呢?在程朱理学中有一句着名度极高的话,让人又爱又恨的话,这句话就是朱熹同志解决棘手问题的办法:“存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的意思不单单只是叫失去丈夫的妇女们不要改嫁,它告诉我们要用理性的客观的主宰万物的“理”,去对抗去消灭我们主观上心中的“欲”,只有这样做,世界才和谐。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追求那个高远的绝对正确的“理”,然后放弃掉我们自身狭隘的“欲”。
鉴于朱熹是我们大明王朝皇帝陛下理论上的祖宗,鉴于大明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这套理论成为了大明官方的核心价值体系,不单是各级政府机构按此价值观办事,各级教育系统也按此价值观教书育人,如果说“理”是世界的绝对真理,那么理学在当时的政坛文坛也是绝对真理。经过九年的格物致知,王守仁先生对这个探求“理”的方法产生了动摇,而接下来的事,让他对这个理论体系也产生了怀疑。
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由于身体微恙,王守仁移居杭州静养,面对着淡妆浓抹的绝美西湖他的心情有了难得的轻松,尽管心里的结尚未解开,可能够纵情于山水忘怀心中之忧愁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他抛开了之前消极的情绪,时常往返于各大寺庙书院,与得到高僧或是知名文人畅谈人生,生活颇丰。
有一天王守仁留宿一座古寺,他遇见了一位年老的僧人,那僧人端坐佛堂闭母凝神,一看便是得道之高僧,一旁的小和尚对他说:“这个大和尚从不曾开口说话,也不曾睁眼看人,如此已有三年了。”王守仁沉默了半晌,突然大喝一声,怒斥道:“你这老和尚整天唧唧歪歪说些什么!整天瞪着眼睛眼睁睁得看着什么!”这句话甚有玄机,因为那大和尚明明就三年不曾开口三年不曾睁眼了,和尚大吃一惊,因为这三年来从不曾有一人朝他如此大喝,也不曾有人和他说过如此玄妙的话,于是他缓缓的睁开了眼睛,四目一对,口称:“居士别来无恙。”二人开始了交谈,他们从佛经开始,谈到西湖,又谈到了佛家所言之道,那大和尚果然是一代高僧,对佛法的理解大大超出了王守仁的意料,聊着聊着,王守仁突然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